臨床神經解剖學研究—過去、現在、未來(上篇)
神經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陳劭青
摘要:
在伊斯坦堡進行了一年的神經解剖學研究,完全顛覆過去我對神經解剖學這門學問的狹隘觀點;鑑往知來,更深刻體認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少走好多冤枉路。如今學界相當重視論文發表,固然在推進人類知識邊際上多有助益,但若是忽略了「書本」—數千年來始終作為人類知識傳承的重要媒介—則難免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於進修期間,我才發現當今神經外科教皇Prof. Yasargil 對神經外科界所做出的每一項貢獻,其實都站在前人的基礎上,而他個人橫跨數百年、超過兩萬冊的腦科學藏書,正是他助他站上巔峰的翼下之風!
此外我於進修期間亦參訪了北美近十年來皆蟬聯第一名的神外訓練中心,最令我印象深刻有三點:一是名滿天下的訓練中心(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竟是依附於地區小醫院的私人集團、二是這樣小的醫院也有自己的神經外科圖書館、三是集團CEO (相當於Chairman)每週至少三天,每次至少1-2小時親自與住院醫師討論病例及分享個人經驗,讓我對「傳承」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臺北榮總走過一甲子的歲月,在前人的努力下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醫學中心;展望未來、邁向百年,如何延續北榮的榮光,於繁花之上再生繁花,我想對知識、技術及歷史的傳承格外值得關注。
關鍵字:神經、外科、解剖、訓練、傳承、歷史
一、目的
神經解剖學知識為神經外科手術之根基,素來為神經外科醫師所重。若論及當代臨床神經解剖學重鎮,神經外科醫師們多半會立刻聯想到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Rhoton教授的實驗室;但若是提到當代最偉大的神經外科醫師,則全世界所有的神經外科醫師大概無一例外的會一致推崇94歲高齡仍於伊斯坦堡執教的 Yasargil教授!這兩位教授的傳承與理念雖不盡相同,卻共同影響了至少三代的神經外科醫師。
我於住院醫師期間有幸受教於Yasargil教授的學生,並與Rhoton教授的學生多所接觸,即已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幸運;然而即使如此,兩位教授的學生皆一致推薦我還是應該趁著Yasargil教授仍在世,到伊斯坦堡親炙其大師風範。經過一年在伊斯坦堡的學習,我終於深刻體會顏淵當年的心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雖然一年的時間太短,絕不足以盡窺亞氏學說之堂奧,但回想進修前對神經解剖學的觀點之狹隘,雖深感慚愧,亦自覺一年來精進不少;比起當初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至少我已略知Yasargil學派千年傳承之脈絡,知道將往何處尋寶。以下將略述此一傳承之源起、今日發展,以及未來展望,更重要的是從Yasargil教授一生的傳奇經歷中,尋找在此瞬息萬變的資訊爆炸時代,一個能幫助臺北榮總神經外科安身立命、繼往開來的啟發!
二、過程
一般公認西方醫學之父為活躍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0 B.C.),然而事實上希波克拉底並無留下手稿、行醫紀錄、或是直接受業於他的學生;但在公元前三世紀建立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內(Library of Alexandria),有一個編目囊括了許多關於醫學的文獻,稱之為「希波克拉底輯錄」(Corpus Hippocrates);因此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皆把希波克拉底輯錄視為希波克拉底的直接貢獻,並把亞歷山卓圖書館此一傳承視為希波克拉底醫學院!
繼承亞歷山大大帝埃及領土的托勒密王朝,仿照亞里斯多德雅典學院為樣板,透過重金收購、掠奪、抄寫等手段,在亞歷山大城建立了當時世界上藏書最多、書目最齊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並同時設立數學、醫學、文學、天文學四個學院,廣邀國際知名學者主持。在王室的支持下,亞歷山大城很快成為國際文化中心,人文薈萃、所有知名的國際學者皆集中至此處講學、授課、並進行研究。
The Great Library of Alexandria, O. Von Corven, 19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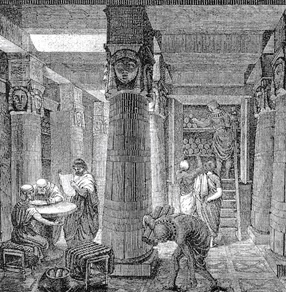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rary_of_Alexandria
亞歷山大鼎盛時期最富盛名的醫師—希羅菲盧斯 (Hirophilus) 出生於今天土耳其伊斯坦堡的亞州岸卡迪柯伊 (Kadikoy),是公認的第一位神經解剖學家,據說當時各國的貴族政要若患疾病,皆不遠千里至亞歷山大城向他求診。他藉由解剖學研究,發現所有的神經皆可追溯至腦,因而提出人類意識源自於腦,而非亞里斯多德以前的哲學家所主張的心源說,他也是第一位描述不同腦室構造的醫師,他認為人類的靈魂就居住在四腦室底下半部。西方醫學因為解剖學的研究及所取得的成果,在這個時期有長足的進步。
而若要談及西方醫學史上近兩千年來最具影響力的醫師,則非蓋倫 (Galen) 莫屬;在他之後約有近1500年的時間,沒有超越蓋倫時代的醫學論述出現,直到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以後,西方世界才對人體再次地感興趣,將注意力從「神」轉移到「人」身上。蓋倫出生於西元二世紀羅馬帝國的Pergamon,是今天土耳其小亞細亞距愛琴海約26公里的帕加馬 (Bergama),他曾於年輕時至亞歷山大進修約10年,並終身將自己視為希波克拉底及希羅菲盧斯學派的繼承者。在他「論解剖」(On Anatomical Procedures) 一文中曾留下他對進修的看法:
請慎重考慮別只是從書本上學習解剖學知識,請試著親自仔細的檢視一切解剖構造……要做到這些在亞歷山大並不困難……因此,如果沒有更好的選擇,請試著到亞歷山大城去。
結束亞歷山大城的學業之後,蓋倫首先回到家鄉去,成為羅馬角鬥士 (Gladiator) 的治療師;他驚人的療效很快引起注意,並將他帶至羅馬且成為御醫。然而,終其一生,因為羅馬帝國的禁令,蓋倫不再有機會進行人體解剖,而必須使用猿猴或是公牛作為替代品,這也成為1400年後,他飽受維薩里 (Andre Vesalius)詬病的主因。

Andre Vesalius &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eas_Vesalius
西方醫學再次有重大突破得等到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當維薩里再次對人體進行解剖。儘管維薩里對蓋倫的每一項解剖發現做更深入的描述時常不忘批評蓋倫及其學生滿足於利用動物解剖研究標本,或者因為忽略某些細節而沒能做出更正確的論述,但無疑維薩里是蓋倫的頭號粉絲。不僅他將許多蓋倫的手稿從希臘文翻譯成拉丁文、他自己的書「人體的構成」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寫作形式模仿蓋倫的著作,更在書中稱呼蓋倫為「神聖的蓋倫」!下面這段書中的描述更能看出他對蓋倫的推崇:
在許多義大利大學,有些人傲慢地將(穹窿體)視為大腦蚓部,並因此宣稱自己有了重大發現。在此我必須限制我自己繼續談及這些無能的解剖學家:他們不僅是徹底的無知而且他們所宣稱的重大發現不僅毫不重要還對醫學一點貢獻也沒有。更有甚者,他們費盡千辛萬苦才證明的錯誤的、瑣碎的知識,事實上早已被蓋倫優雅並準確的描述了。
然而即使是偉大的維薩里也沒能夠回答千年前蓋倫的疑問:穹窿體 (Fornix) 究竟源自哪裡?又終於何處?但是維薩里的學生做到了。法洛里(Costanzo Varolio) 一改千年來皆把腦留在顱骨內檢視的傳統,首先將腦拿到顱骨外,由下往上檢視,不僅找到了穹窿體的起源—海馬迴,更重要的是這個步驟開啟了解剖學新的篇章!醫學的突破往往伴隨著新技術的採用,在此基礎上法洛里第一次準確的描述了橋腦 (Pons) ,也因為同樣的技術,英國醫師威利斯 (Thomas Willis)才注意到顱底的大腦動脈環 (Circle of Willis),並將環繞腦幹周圍的腦迴稱為「邊緣」(Limbus),當時他大概沒想過近三百年後對「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 的猜想會成為人類對腦功能研究的濫觴。
十七世紀初出現了另一個技術性的突破,即對標本處理方式的改善。義大利解剖學家馬爾皮吉 (Marcello Malpighi) 率先將腦放入沸水中煮熟,從而延長了標本保存時間;另一位法國醫生維尤斯 (Raymond Vieussens) 改進了他的作法,將腦放入油中煮,因此更好的保存了神經纖維束,並出版了第一本神經纖維束的圖譜。從此時開始直到二十世紀中,約有三百年的時間,從事腦神經纖維解剖一直是研究巨觀腦解剖的主流方式,也因為此一技術,十八世紀的達吉爾 (Felix Vicq D’azyr) 在法洛里找到穹窿體起源的兩百年後,終於能答出蓋倫千年一問的另一半答案:穹窿體的終點在乳頭體 (Mammilary Body)。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葉後,有將近五十年的時間,少有人再進行神經纖維束的解剖研究,直到二十一世紀腦磁振造影技術(MRI)中擴散張量影像(DTI)的發展,才再次勾起了人們對尋找神經纖維束的關注。
十九世紀是神經解剖學大放異彩的時刻。經過兩千年對腦部「結構」的研究,人類直至此時才終於有足夠的基礎開始探問如今令無數腦科學家著迷的問題:如何分辨腦部不同的功能區,他們彼此之間又如何協同運作?關於腦功能的猜想一樣始於穹窿體。兩千年來,西方解剖學家們一直認為穹窿體是上帝極偉大的創造,他就像屋子的橫梁一樣,不僅構成了三腦室頂,也撐起了側腦室,而腦室內流淌的、清澈的腦脊隨液即是人類意識的泉源;相比之下,佔據顱內極大空間的腦實質,則並未受到太多關注。直到十九世紀初,才開始有解剖學家懷疑與海馬迴相連的穹窿體,該不會跟人類記憶也有關吧?而對穹窿體的研究,儘管許多解剖學家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且終被證明是錯誤的,如Papez Circuit、Jacob Circuit,但在這些基礎上我們終於逐漸掌握了人類對於記憶、慾望、情緒控管極基礎的知識—邊緣系統的存在。
十九世紀另一個腦解剖學發展的重要分支是腦皮層細胞結構學 (Cytoarchitecture),始於梅涅特 ( Meynert) 率先將腦皮層拿至顯微鏡下觀察,發現原來並非整個腦的皮層細胞排列方式都相同,而是在不同區域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布羅德曼 (Brodmann) 以相同的研究方式提出了根據細胞結構並整合腦功能區,將大腦劃分為一系列解剖區域的布羅德曼分區 (Brodmann Area)。此種技術受到許多解剖學家的重視並持續改良,於二十世紀中葉前一直是研究腦功能分區及顯微解剖學的重要工具,然而隨著神經刺激術的發展及其對腦功能分區研究的影響,細胞結構學的研究也逐漸淡出臨床醫師的視角,不再受到太多重視,直到二十一世紀,當3T MRI的解析力提高,解剖學家能用磁振造影進行皮層結構區塊分析,細胞結構學的知識才又再次受到重視。

Brodmann Are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odmann_area
談到十九世紀的科學發展,另一個不能不談的學說即是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所提出的演化論。即使從一開始便飽受教會的攻擊,然而還是不能阻止科學家們去探索、驗證達爾文學說的好奇心,並因此衍生了幾個不同的學門;其中,比較解剖學這門學問對神經解剖領域起了非常深遠的影響。藉由觀察不同物種的胚胎發育過程及其系統發生學上的演化距離、重演論的研究,解剖學家對於腦部構造的理解不再止於發育完成的成人腦部狀態,而是涵蓋了人類腦部演化、胚胎發育的歷史,對於各項疾病可能的起源、可能的存在方式,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註)

George Romanes's 1892 copy of Ernst Haeckel's controversial embryo drawings
en.wikipedia.org/wiki/Recapitulation_theory
甚至,因為遺傳學、細胞學、分子生物學一日千里的進展,如今的神經解剖學已經進展到基因的層次—連達爾文大概也未曾想像過,即使是與我們看來差異如此巨大、在演化樹上親緣關係極遠的果蠅,一樣透過幾個類似的基因來調控體節;而人類的體節,即是不同的脊椎節數。
人類的醫學技術在近百年內取得極大的進展,神經外科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學門—專科化約莫只有百來年的歷史—其日新月異的突破自是令人時刻感到興奮,特別是近三十年來電腦斷層及磁振造影術的發展,更大大開拓了神經外科醫師的眼界,全方面的提升了神經外科手術治療疾病的各種可能性。當我們沉醉於新科技所帶來的新知識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前人所做出的卓越貢獻;若是深入檢視過去科學家們窮盡畢生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很容易便能找到與今日最新科學發展之間的連結,並獲得不同的啟發。畢竟所有重大的科學發展,無一不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之上,一步一步向前;相信即使是神聖的蓋倫、抑或偉大的維薩里,也會支持此一觀點。
註:於1870年由海克爾 (Ernst Haeckel) 提出的重演論認為不同物種在同一段發育時期的差異也會顯現出這些物種在演化上的親近程度,而且這些生物演化歷史的重複表現,能夠出現在任何生物的胚胎發育過程。此學說已於1997年被正式推翻,因其雖然經常發生,但並非是一個自然規律。
因字數篇幅,本文分上、下兩篇出刊。本文為上篇。
最後更新: